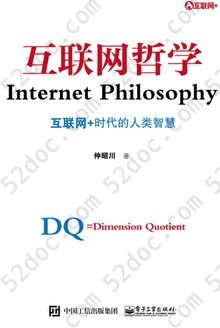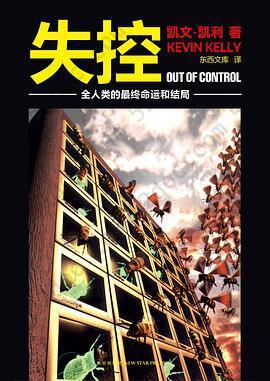注重体验与质量的电子书资源下载网站
分类于: 设计 云计算&大数据
简介

与神为友: 全新修订版 豆 8.2分
资源最后更新于 2020-08-26 15:23:07
作者:[美]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
译者:李继宏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6-01
ISBN:9787210081180
文件格式: pdf
标签: 自我成长 我想读这本书 神学 灵修 很棒的书 哲学 真相 好书,值得一读
简介· · · · · ·
【内容简介】
来吧,坐下来聊聊天,让我们成为朋友。
终于不再孤单,需要帮助时永远不会孤立无援。
婚姻终结、事业停顿、健康恶化,他曾一度游走在慢性抑郁症边缘。
尼尔·唐纳德·沃尔什在这本书里写下自己的故事。
他小时候特别喜欢弹钢琴,遭到父亲无情扼杀;
当厌班的情绪高涨时,意外被“绑架”;
大火之后身无分文,求助前妻却被拒之门外,因一份特别的礼物,重启人生。
如果说,《与神对话》像导师,帮我们重新认识自己,以及和这个世界、宇宙的关系,
那么,这本书则更像是知己,娓娓道来,提供具体解决方法。
他的故事,或许也是我们共同的故事,愿我们都能清醒地生活着。
【编辑推荐】
1996年11月24日《与神对话》悄然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位居非虚构类第14位,上榜长达137周,拥有37种语言译本,成为不可动摇的殿堂级经典著作。用著名作家刘同的话说,这是“让一个人...
目录
【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别以为那就不是礼物
有时候我很难爱自己。尤其是当我想起我从前的所作所为时。我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我有整整三十年是个彻头彻尾的……
好吧,也许我以前不算彻头彻尾的——算了,不说了……但我肯定非常不善于让人们找到安全感。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如此,当时我以为我对个人成长有所了解,却没有应用我学到的道理。
离开泰丽·科尔—惠特克传教会之后,我又结了婚,并从圣迭戈的郊区移居华盛顿州的小城克里奇塔特。但我在那里的日子过得不是很如意,主要是因为我是个不能提供安全感的人。我很自私,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尽可能地去摆布每个人。
后来我搬家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希望有个新的开始,但情况也没改善。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从复杂变得更加复杂,我和我妻子住的公寓楼突然发生大火,把我们所有的家当烧个精光。但我尚未坠入谷底。我拆散我的婚姻,建立其他几段关系,又把它们拆散。我就像落水的人,挣扎着要浮起来,却几乎将身边的每个人都拖下水。
那时我以为我已经惨得不能再惨了。但我错了。有个八十岁的老人开着一辆斯图贝克,迎头撞上我驾驶的轿车,害我脖子骨折。结果我戴了超过一年的颈圈,起初几个月,我每天都要去接受高强度的物理治疗,随后几个月是两天去一次,后来是每周去两次,最后疗程终于完了——但我生活中别的一切也都完了。我丧失了赚钱的能力,失去了最近的一段婚姻;有一天我走出家门,发现我的轿车被偷走了。
这就是典型的“屋漏偏遭连夜雨”,我想我余生再也忘不掉那段日子。当时我仍在为其他不如意之事气苦,徒劳地在街道上来回寻觅,希望我只是忘记把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后来我彻底放弃了,心里感到极其痛苦,扑通跪在人行道上,发出了愤怒的嚎叫。有个路过的女人吃惊地看着我,匆忙跑到街道的另一边。
几天后,我带着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前往南俄勒冈的车票,我有三个孩子跟他们的母亲生活在那边。我问她能否帮帮忙,也许可以让我在她家的空房间暂住几个星期,然后我会想办法搬出去。她合情合理地拒绝了我,把我赶出门外。我跟她说我走投无路了,她说:“你可以把帐篷和野炊器具拿走。”
于是我沦落到了俄勒冈州阿什兰市郊外杰克逊温泉公园的中央大草坪,那里每周的租金是25美元,但我连这点钱都没有。我恳求宿营地的经理宽限几天,让我可以去筹措一些钱。他显得很为难。公园里寄居客已经人满为患,他不希望再有人来凑热闹,但他听了我的倾诉。他听说了祝融之灾、飞来横祸、脖子骨折、汽车失窃,以及各种接二连三的倒霉事,我想他心软了。“好吧,”他说,“你先住几天。看看你能怎么解决。把帐篷搭在那边。”
那年我四十五岁,我觉得我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我曾是薪俸不菲的播音员、报纸的执行主编、某个全国性连锁学校的公共关系主管、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的私人助理,如今却在公园里为了五分钱收集啤酒罐和汽水瓶。(二十个啤酒罐可以换一块钱,一百个就是五块钱,五个五块钱就能让我在宿营地住一个星期。)
我在温泉公园度过了大半年,这段露宿街头的日子让我学到了不少生活知识。其实不算真的露宿街头,但也差不多了。我发现那些流落在野外、街头、桥底和公园的人有一种守则,如果这星球上其他人都遵守它,那么它能改变世界。这个守则就是:相互帮助。
如果你流落在外超过几个星期,你会认识其他无家可归的人,而他们也会认识你。要注意的是,没有人会问你怎么会沦落至此。但如果发现你有麻烦,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而许多有家有室的人则会。他们会停下来问:“你还好吧?”如果你需要帮忙,他们又帮得上的话,那么你会如愿的。
在街头上,曾经有人把他们最后一双干袜子送给我,有时候我捡的啤酒罐不够“份额”,别人就把他们捡到的一半分给我。如果有人赚了大钱(某个路人施舍了五块或者十块),他会买了食物,回到宿营地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搭帐篷时的情景。我到营地时已是黄昏。我知道我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又没有太多搭帐篷的经验。当时风越吹越大,似乎就要下雨。
“搭在那棵树下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然后再用绳子绑住那根电线杆。绳子上弄个显眼的标记,这样你半夜起来上厕所就不会把自己绊倒。”
天空飘起细雨。突然间,我们一起搭帐篷。这位无名的朋友并不多嘴,他只会说诸如“这边得打一根桩”和“最好把门帘拉起来,否则你会睡在湖里”之类的话。
把帐篷搭好之后(其实大部分活是他干的),他把我的铁锤扔在地上。“应该很牢固啦,”他说着就走开了。
“喂,谢谢你,”我在他身后大声说,“你叫什么名字?”
“没关系啦,”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再也没有看到他。
在公园里,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遇到最大的难题(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是保持温暖和干燥。我不为升职而渴望,不为“泡妞”而焦躁,不为电话账单而烦恼,也不问余生将要做什么。当时经常下雨,三月的寒风阵阵吹来,我只想要让自己保持温暖和干燥。
我有时会想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但大多数时候是在想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如果你一无所有,每周要赚二十五美元是很难的。当然,我也想过要找工作。但那时我真的是朝不保夕,正处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我的脖子尚未完全康复,我没有车、没有钱,食物很少,也没有居所。幸运的是,那时是春天,夏天很快就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每天都去翻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报纸,半个别人没吃完的苹果,或者小学生扔掉的包着三明治的午餐袋。报纸可以垫在帐篷下面。它有保暖作用,能防止水渗进来,也能让坑坑洼洼的地面变得更加蓬松柔软。不过更重要的是,它是招聘信息的来源。每次捡到报纸,我都要看分类广告,寻找合适的工作。由于我脖子有伤,很重的体力活我是干不了的,但男人能够立刻找到的工作又大多数是体力活。比如说日班工人,或者这个机组那个机组的帮工。但经过两个月的发掘,我挖到了矿藏。
播音员/周末兼职
必须有工作经验
请致电:××××××
我很激动。在俄勒冈州梅德福德市这样的小地方,曾经在广播电台工作过但目前失业的人能有多少呢?我跑到公用电话亭,打开那本凑巧捡到的电话黄页簿,找到广播电台那一页,把一个宝贵的二毫五分硬币投进去,拨打了那个电台的号码。我知道负责招聘的应该是节目主管,但他不在。“他能给你回电话吗?”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当然,”我泰然自若地说,我用极具磁性的广播员声线提道,我是想问问招聘广告的事。“下午四点前我都在。”我给了她公用电话的号码,并挂了电话。随后我在电话亭旁边的地上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等对方回电,可是电话没有响起。
第二天早晨,我在垃圾堆里发现一本平装爱情小说,我捡起它,向电话亭走去。我准备有必要的话就在那里等上一整天。九点时,我坐下,翻开我的书。我心里想,要是中午前电话还没来,过了午餐时间我就用另外一个两毫五分硬币,再打电话过去。电话响起时是九点三十五分。
“很抱歉昨天没有给你回电,”节目主管说,“我事情太多了。听说你看到我们招聘周末播音员的广告。你有经验吗?”
我再次用上播音时的低沉声线。“嗯,我曾在几个地方的广播电台做过,”我漫不经心地说,然后补充道,“做了有二十年啦。”在跟对方交谈时,我祈祷在我站着说话时千万别有大型的房车轰鸣着开进公园。我可不想解释我的客厅里为什么会有大型的车辆。
“你何不来谈谈?”节目主管邀请我,“你有播音带吗?”
播音带是记录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工作时的录音带,但消除了背景音乐。我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没有,我把所有东西都留在波特兰了,”我编造着说,“但我可以‘直播’你给我的任何材料,我认为你会清楚我能干什么。”
“好的,”他同意了,“三点来这里。我四点就走了,所以别太晚到。”
“知道。”
踏出电话亭时,我真的腾空而起,发出了一声欢乐的叫喊。有两个家伙正好从我身边走过。“有什么好消息吗?”其中一个问。
“我找到工作啦!”我兴奋地说。
他们真心为我高兴。“做什么啊?”另外一个想知道。
“去电台做周末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三点钟要去面试。”
“你就这样去面试?”
我还没想到我的尊容。我有几个星期没剪头发,但这也许能说得过去。美国有过半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留着马尾辫。但我必须把衣服处理一下。宿营地有洗衣房,可是我没有买肥皂、洗衣服、烘干衣服的钱,再说我还要买去梅德福德的来回车票。
这时我才想起来自己有多么穷。如果没有发生某些奇迹,我连最基本的事情,比如说到市区面试,都做不了。彼时彼地,我才体会到沦落街头的人想要重新站起来,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有多难。
那两个人盯着我看,仿佛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你没有钱,对吧?”其中一个人有点藐视地问。
“有几块钱吧,”我说,这很可能是言过其实。
“好吧,跟我们走,小子。”
我跟着他们走到其他人搭起的一圈帐篷。“他有机会可以脱离这里,”他们向他们的朋友解释着,并说了几句我没听清的话。然后,两人中年纪较大那个转向我,粗声粗气地问:“你有体面的衣服可以穿吗?”
“有的,在我的背包里,但挺脏的,不能穿。”
“去把你的衣服带过来。”
我回到那个地方,发现多了一个我在温泉公园见到过的女人。她住在公园零星几辆小型拖车中的一辆里。“亲爱的,你去把这些东西洗净烘干,然后我来替你熨好,”她大声地说。
有个男的走上前来,交给我一个棕色的小纸袋,里面有硬币叮当作响。“大家凑了这么多钱,”他解释说,“去洗你的衣服吧。”
五个小时后,我神清气爽、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广播电台,仿佛我刚从高档公寓里走出来。
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这份工作的时薪是6.25元,每周两天,每天八小时,”节目主管说,“很抱歉薪水只有这么多。你水平太高了,如果你拒绝这份工作,我会理解的。”
每周一百元!我居然每周能赚一百元。那可是每月四百元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绝对是一笔财富。“不,不,这正好是我现在想要的,”我随意地说,“我很喜欢当播音员,现在我不做这行了。我只是希望有办法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这对我来说会很有乐趣。”
我没有说谎,因为这确实很有乐趣。绝处逢生的乐趣。我在帐篷里又住了几个月,有了足够的积蓄,于是花三百块钱给我自己买了一辆1963年的纳什漫游者。我有百万富翁的感觉。我们那个宿营地的住客只有我拥有小轿车和固定的收入,我大方地与其他人分享这两样东西,从未忘记他们对我的恩情。
由于担心天气变冷,我在11月住进公园里一座单卧室的小木屋,每周租金七十五元。我很愧疚把我的朋友留在外面(他们付不起这么多钱),所以我会在非常寒冷或者下雨的夜晚邀请一两位来分享我的空间。我设法轮流邀请他们,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避开恶劣的天气。
就在我以为我会永远兼职下去时,我得到了惊喜的邀请:城里另外一家电台请我去主持每天下班高峰时段的节目。他们收听过我周末的节目,很喜欢我的播音——但梅德福德的广播市场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起薪是每月九百元。尽管如此,我又拥有全职的工作,并且有能力离开宿营地了。我在那里生活了九个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光阴。
我祝福我拖着野营装备、步履沉重地走进公园的那天,因为它根本不是我的人生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公园里,我明白了什么是忠厚、诚实、真挚和信任,也明白了什么是简朴、分享和生存。我学会了在永不言败的同时,也接受此时此地的境况,并为之而感恩。
所以我不仅向电影明星和著名作家学习。我的学习对象包括那些和我成为朋友的无家可归者,我每天看到的平凡人,我这一生中邂逅的普通人。例如邮递员,杂货店收银员和干洗店的女职员。
他们都有知识可以教给你,他们都有礼物可以送给你。这里有个伟大的秘密:他们来到人世,也是为了从你手里得到礼物。
你馈赠给他们什么礼物呢?如果你认为你做过伤害他们的糊涂事,也别以为那就不是礼物。它可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就像你在公园里度过的那些日子。
有时候,你从最大的伤痛中学到的,比你从最大的快乐中学到的要多得多,难道你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吗?那么,在你的生活中,谁是迫害者,谁又是受害者呢?
若是达到真正的大师境界,你将会在认识到某种经验的结果之前而不是之后,就能明白答案。
那段穷困潦倒的岁月让你明白,你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永远不要认为你的人生已经完了,要永远记住,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是新的开始,新的机会,重新创造你自己的良机。
哪怕你在弥留之际,哪怕你即将离开人世,只要你决意改过自新,在神看来,你的整个人生就是可取的,光荣的。
哪怕你是恶贯满盈的罪犯,哪怕你是等待行刑或者正在走向刑场的死囚,这依然是真的。
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你必须相信它。如果事实不是如此,我不会这么对你说。
别以为那就不是礼物
有时候我很难爱自己。尤其是当我想起我从前的所作所为时。我这辈子大多数时候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我有整整三十年是个彻头彻尾的……
好吧,也许我以前不算彻头彻尾的——算了,不说了……但我肯定非常不善于让人们找到安全感。甚至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仍然如此,当时我以为我对个人成长有所了解,却没有应用我学到的道理。
离开泰丽·科尔—惠特克传教会之后,我又结了婚,并从圣迭戈的郊区移居华盛顿州的小城克里奇塔特。但我在那里的日子过得不是很如意,主要是因为我是个不能提供安全感的人。我很自私,为了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会尽可能地去摆布每个人。
后来我搬家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希望有个新的开始,但情况也没改善。我的生活不但没有改善,而且还从复杂变得更加复杂,我和我妻子住的公寓楼突然发生大火,把我们所有的家当烧个精光。但我尚未坠入谷底。我拆散我的婚姻,建立其他几段关系,又把它们拆散。我就像落水的人,挣扎着要浮起来,却几乎将身边的每个人都拖下水。
那时我以为我已经惨得不能再惨了。但我错了。有个八十岁的老人开着一辆斯图贝克,迎头撞上我驾驶的轿车,害我脖子骨折。结果我戴了超过一年的颈圈,起初几个月,我每天都要去接受高强度的物理治疗,随后几个月是两天去一次,后来是每周去两次,最后疗程终于完了——但我生活中别的一切也都完了。我丧失了赚钱的能力,失去了最近的一段婚姻;有一天我走出家门,发现我的轿车被偷走了。
这就是典型的“屋漏偏遭连夜雨”,我想我余生再也忘不掉那段日子。当时我仍在为其他不如意之事气苦,徒劳地在街道上来回寻觅,希望我只是忘记把车停在什么地方了。后来我彻底放弃了,心里感到极其痛苦,扑通跪在人行道上,发出了愤怒的嚎叫。有个路过的女人吃惊地看着我,匆忙跑到街道的另一边。
几天后,我带着仅剩的一点钱,买了前往南俄勒冈的车票,我有三个孩子跟他们的母亲生活在那边。我问她能否帮帮忙,也许可以让我在她家的空房间暂住几个星期,然后我会想办法搬出去。她合情合理地拒绝了我,把我赶出门外。我跟她说我走投无路了,她说:“你可以把帐篷和野炊器具拿走。”
于是我沦落到了俄勒冈州阿什兰市郊外杰克逊温泉公园的中央大草坪,那里每周的租金是25美元,但我连这点钱都没有。我恳求宿营地的经理宽限几天,让我可以去筹措一些钱。他显得很为难。公园里寄居客已经人满为患,他不希望再有人来凑热闹,但他听了我的倾诉。他听说了祝融之灾、飞来横祸、脖子骨折、汽车失窃,以及各种接二连三的倒霉事,我想他心软了。“好吧,”他说,“你先住几天。看看你能怎么解决。把帐篷搭在那边。”
那年我四十五岁,我觉得我的生活走到了尽头。我曾是薪俸不菲的播音员、报纸的执行主编、某个全国性连锁学校的公共关系主管、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博士的私人助理,如今却在公园里为了五分钱收集啤酒罐和汽水瓶。(二十个啤酒罐可以换一块钱,一百个就是五块钱,五个五块钱就能让我在宿营地住一个星期。)
我在温泉公园度过了大半年,这段露宿街头的日子让我学到了不少生活知识。其实不算真的露宿街头,但也差不多了。我发现那些流落在野外、街头、桥底和公园的人有一种守则,如果这星球上其他人都遵守它,那么它能改变世界。这个守则就是:相互帮助。
如果你流落在外超过几个星期,你会认识其他无家可归的人,而他们也会认识你。要注意的是,没有人会问你怎么会沦落至此。但如果发现你有麻烦,他们不会袖手旁观,而许多有家有室的人则会。他们会停下来问:“你还好吧?”如果你需要帮忙,他们又帮得上的话,那么你会如愿的。
在街头上,曾经有人把他们最后一双干袜子送给我,有时候我捡的啤酒罐不够“份额”,别人就把他们捡到的一半分给我。如果有人赚了大钱(某个路人施舍了五块或者十块),他会买了食物,回到宿营地跟大家分享。
我记得第一天晚上搭帐篷时的情景。我到营地时已是黄昏。我知道我必须加快速度,可是又没有太多搭帐篷的经验。当时风越吹越大,似乎就要下雨。
“搭在那棵树下面,”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传来一个嘶哑的声音,“然后再用绳子绑住那根电线杆。绳子上弄个显眼的标记,这样你半夜起来上厕所就不会把自己绊倒。”
天空飘起细雨。突然间,我们一起搭帐篷。这位无名的朋友并不多嘴,他只会说诸如“这边得打一根桩”和“最好把门帘拉起来,否则你会睡在湖里”之类的话。
把帐篷搭好之后(其实大部分活是他干的),他把我的铁锤扔在地上。“应该很牢固啦,”他说着就走开了。
“喂,谢谢你,”我在他身后大声说,“你叫什么名字?”
“没关系啦,”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再也没有看到他。
在公园里,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我遇到最大的难题(也是我最大的愿望)是保持温暖和干燥。我不为升职而渴望,不为“泡妞”而焦躁,不为电话账单而烦恼,也不问余生将要做什么。当时经常下雨,三月的寒风阵阵吹来,我只想要让自己保持温暖和干燥。
我有时会想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但大多数时候是在想我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如果你一无所有,每周要赚二十五美元是很难的。当然,我也想过要找工作。但那时我真的是朝不保夕,正处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状态。我的脖子尚未完全康复,我没有车、没有钱,食物很少,也没有居所。幸运的是,那时是春天,夏天很快就来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
我每天都去翻垃圾桶,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报纸,半个别人没吃完的苹果,或者小学生扔掉的包着三明治的午餐袋。报纸可以垫在帐篷下面。它有保暖作用,能防止水渗进来,也能让坑坑洼洼的地面变得更加蓬松柔软。不过更重要的是,它是招聘信息的来源。每次捡到报纸,我都要看分类广告,寻找合适的工作。由于我脖子有伤,很重的体力活我是干不了的,但男人能够立刻找到的工作又大多数是体力活。比如说日班工人,或者这个机组那个机组的帮工。但经过两个月的发掘,我挖到了矿藏。
播音员/周末兼职
必须有工作经验
请致电:××××××
我很激动。在俄勒冈州梅德福德市这样的小地方,曾经在广播电台工作过但目前失业的人能有多少呢?我跑到公用电话亭,打开那本凑巧捡到的电话黄页簿,找到广播电台那一页,把一个宝贵的二毫五分硬币投进去,拨打了那个电台的号码。我知道负责招聘的应该是节目主管,但他不在。“他能给你回电话吗?”有个女人的声音问。
“当然,”我泰然自若地说,我用极具磁性的广播员声线提道,我是想问问招聘广告的事。“下午四点前我都在。”我给了她公用电话的号码,并挂了电话。随后我在电话亭旁边的地上坐了整整三个小时,等对方回电,可是电话没有响起。
第二天早晨,我在垃圾堆里发现一本平装爱情小说,我捡起它,向电话亭走去。我准备有必要的话就在那里等上一整天。九点时,我坐下,翻开我的书。我心里想,要是中午前电话还没来,过了午餐时间我就用另外一个两毫五分硬币,再打电话过去。电话响起时是九点三十五分。
“很抱歉昨天没有给你回电,”节目主管说,“我事情太多了。听说你看到我们招聘周末播音员的广告。你有经验吗?”
我再次用上播音时的低沉声线。“嗯,我曾在几个地方的广播电台做过,”我漫不经心地说,然后补充道,“做了有二十年啦。”在跟对方交谈时,我祈祷在我站着说话时千万别有大型的房车轰鸣着开进公园。我可不想解释我的客厅里为什么会有大型的车辆。
“你何不来谈谈?”节目主管邀请我,“你有播音带吗?”
播音带是记录广播电台的音乐节目主持人在工作时的录音带,但消除了背景音乐。我肯定引起了他的兴趣。
“没有,我把所有东西都留在波特兰了,”我编造着说,“但我可以‘直播’你给我的任何材料,我认为你会清楚我能干什么。”
“好的,”他同意了,“三点来这里。我四点就走了,所以别太晚到。”
“知道。”
踏出电话亭时,我真的腾空而起,发出了一声欢乐的叫喊。有两个家伙正好从我身边走过。“有什么好消息吗?”其中一个问。
“我找到工作啦!”我兴奋地说。
他们真心为我高兴。“做什么啊?”另外一个想知道。
“去电台做周末音乐节目主持人!我三点钟要去面试。”
“你就这样去面试?”
我还没想到我的尊容。我有几个星期没剪头发,但这也许能说得过去。美国有过半的音乐节目主持人留着马尾辫。但我必须把衣服处理一下。宿营地有洗衣房,可是我没有买肥皂、洗衣服、烘干衣服的钱,再说我还要买去梅德福德的来回车票。
这时我才想起来自己有多么穷。如果没有发生某些奇迹,我连最基本的事情,比如说到市区面试,都做不了。彼时彼地,我才体会到沦落街头的人想要重新站起来,重新过上正常的生活有多难。
那两个人盯着我看,仿佛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
“你没有钱,对吧?”其中一个人有点藐视地问。
“有几块钱吧,”我说,这很可能是言过其实。
“好吧,跟我们走,小子。”
我跟着他们走到其他人搭起的一圈帐篷。“他有机会可以脱离这里,”他们向他们的朋友解释着,并说了几句我没听清的话。然后,两人中年纪较大那个转向我,粗声粗气地问:“你有体面的衣服可以穿吗?”
“有的,在我的背包里,但挺脏的,不能穿。”
“去把你的衣服带过来。”
我回到那个地方,发现多了一个我在温泉公园见到过的女人。她住在公园零星几辆小型拖车中的一辆里。“亲爱的,你去把这些东西洗净烘干,然后我来替你熨好,”她大声地说。
有个男的走上前来,交给我一个棕色的小纸袋,里面有硬币叮当作响。“大家凑了这么多钱,”他解释说,“去洗你的衣服吧。”
五个小时后,我神清气爽、衣着光鲜地出现在广播电台,仿佛我刚从高档公寓里走出来。
我得到了那份工作!
“这份工作的时薪是6.25元,每周两天,每天八小时,”节目主管说,“很抱歉薪水只有这么多。你水平太高了,如果你拒绝这份工作,我会理解的。”
每周一百元!我居然每周能赚一百元。那可是每月四百元啊——这对当时的我来说绝对是一笔财富。“不,不,这正好是我现在想要的,”我随意地说,“我很喜欢当播音员,现在我不做这行了。我只是希望有办法可以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这对我来说会很有乐趣。”
我没有说谎,因为这确实很有乐趣。绝处逢生的乐趣。我在帐篷里又住了几个月,有了足够的积蓄,于是花三百块钱给我自己买了一辆1963年的纳什漫游者。我有百万富翁的感觉。我们那个宿营地的住客只有我拥有小轿车和固定的收入,我大方地与其他人分享这两样东西,从未忘记他们对我的恩情。
由于担心天气变冷,我在11月住进公园里一座单卧室的小木屋,每周租金七十五元。我很愧疚把我的朋友留在外面(他们付不起这么多钱),所以我会在非常寒冷或者下雨的夜晚邀请一两位来分享我的空间。我设法轮流邀请他们,这样每个人都有机会避开恶劣的天气。
就在我以为我会永远兼职下去时,我得到了惊喜的邀请:城里另外一家电台请我去主持每天下班高峰时段的节目。他们收听过我周末的节目,很喜欢我的播音——但梅德福德的广播市场不是很大,所以他们给我开出的起薪是每月九百元。尽管如此,我又拥有全职的工作,并且有能力离开宿营地了。我在那里生活了九个月。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段光阴。
我祝福我拖着野营装备、步履沉重地走进公园的那天,因为它根本不是我的人生的终点,而是新的起点。在公园里,我明白了什么是忠厚、诚实、真挚和信任,也明白了什么是简朴、分享和生存。我学会了在永不言败的同时,也接受此时此地的境况,并为之而感恩。
所以我不仅向电影明星和著名作家学习。我的学习对象包括那些和我成为朋友的无家可归者,我每天看到的平凡人,我这一生中邂逅的普通人。例如邮递员,杂货店收银员和干洗店的女职员。
他们都有知识可以教给你,他们都有礼物可以送给你。这里有个伟大的秘密:他们来到人世,也是为了从你手里得到礼物。
你馈赠给他们什么礼物呢?如果你认为你做过伤害他们的糊涂事,也别以为那就不是礼物。它可能是一笔很大的财富,就像你在公园里度过的那些日子。
有时候,你从最大的伤痛中学到的,比你从最大的快乐中学到的要多得多,难道你没有过这样的时候吗?那么,在你的生活中,谁是迫害者,谁又是受害者呢?
若是达到真正的大师境界,你将会在认识到某种经验的结果之前而不是之后,就能明白答案。
那段穷困潦倒的岁月让你明白,你的生活并没有结束。永远不要认为你的人生已经完了,要永远记住,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是新的开始,新的机会,重新创造你自己的良机。
哪怕你在弥留之际,哪怕你即将离开人世,只要你决意改过自新,在神看来,你的整个人生就是可取的,光荣的。
哪怕你是恶贯满盈的罪犯,哪怕你是等待行刑或者正在走向刑场的死囚,这依然是真的。
你必须明白这个道理。你必须相信它。如果事实不是如此,我不会这么对你说。